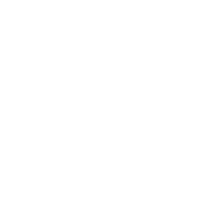奥克兰时尚华城-奥克兰华府美食
2024-06-30 本站作者 【 字体:大 中 小 】
诗歌
灯光暗了,你在哪儿?
文_舒婷

1992年12月,诗人(舒婷)与顾城、谢晔在成都。
1993年10月8日,我们从安娜堡出发,下午5点左右驱车前往爱荷华市中心。我和李典一边抽烟,一边往公用电话投币。平时谭嘉的声音轻柔而缓慢,这次却快了五倍:“……有什么需要,我过来给你带路。”挂断电话后,我们俩都愣住了。我们停下车,穿着米色风衣的谭嘉像迎风而上的鸟儿一样径直向我跑来——大约半小时前,王宇从纽约打来电话,告知我顾城和谢野的噩耗。在谭嘉和家兴的住处,我心神不宁,不知所措。吃过晚饭后,李典开车送我去酒吧。回到家,老板已经睡着,我独自坐在那里,醉醺醺地度过深夜……
世间若有爱,便是开始,亦是结束。1979年初春,北京东四十四条76号(《今日》编辑部),有人敲门,顾城和顾湘走了进来。我们第一次见面。顾城像个孩子,腼腆沉默寡言,顾湘则眼睛发亮,仿佛会说话。兄妹俩刚去过西单“民主墙”,热血沸腾。在顾城的怂恿下,他们直奔《今日》编辑部。从那天起,我们一路走来,时光的长廊一闪而过,在十四年的尽头戛然而止。
1993年10月18日,我在《今天》冬季刊上写了一篇后记:“12月23日,是《今天》创刊十五周年。临近周年之际,我们又一次听到丧钟:顾城、谢野的离去令人震惊,世界显得更加空虚。回首《今天》诞生在白雪皑皑、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里的日子,仿佛是那么遥远,隔着万丈深渊。过去就像一艘即将离去的船,过去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在告别,也在相认。逝去的朋友成了那艘船的主人。”
古今开门,主客相迎,却难相认。
在文字与空白之间,记忆并不十分可靠,但它是真实的:碎片的拼凑或图像的重叠构成了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梦想。
——北岛
1993年10月,我从福建赶赴北京,即将应维也纳大学的邀请飞往奥地利。在福建驻京办事处下榻的酒店里,一位绰号为阿毛的记者来见我。我从来不接受采访,即使是熟人,我也不想破例。临行前,我刚从国外的一个长途电话中得知了这个坏消息,便下楼到大厅与他见面,想了解一下更多细节。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一切信息都很慢而且碎片化。阿毛有记者的敏锐和优势,他先得到消息,知道我正好在北京,便立即赶来试探我。
后来阿毛在短文中写道,我“表情茫然地离开,走进电梯时背脊疲惫而沉重”。
此时,距离顾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诗人顾城
1. 童话诗人
——致 GC
你相信你写的童话
我变成了童话里的蓝色花朵
你的眼睛已经忽略
病树、破墙
生锈的铁栅栏
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号
聚集星星、黄芪和螽斯的队伍
走向无污染的远方
出发
心也许很小
世界很大
所以人们相信你
我相信雨后的松树
有数百万个小太阳悬挂
桑树和鱼竿使河面弯曲
云朵缠住了风筝的尾巴
无数震撼的记忆
抖落时间的尘埃
随着纯银的声音
和你的梦想对话
世界可能很小
心很大
1980.4
这篇标注写于1980年4月的手稿,应该是1981年修改过的。我第一次遇见顾城,是在1980年夏天,在《诗歌杂志社》举办的第一届“青年诗歌节”上。
年轻的诗人们从四面八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北京,虎坊桥《诗歌杂志社》旧址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内有简朴的小楼,还有结满果实的海棠树。
正式报名那天,小小的会议室里人来人往,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径直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一年,顾城24岁。
我得知,这群学生中,有两个是今日的同事。虽然是第一次认识顾城,但我们自然很亲近,仿佛是老乡。顾城拉着我走到走廊,躲在黑暗角落里的江河走了出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手上还带着一股烟味。
我们就这样互相认识了。从此以后,只要他们两个来开会,我们就会相处融洽,形影不离。我们这些外地人,就住在办公室的临时宿舍里,北京的学生只能“上学”。平日里,我们各自写写练练,只有听汇报或者讨论学习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江河几乎从来不来。
《诗刊》不提供餐食,我们被安排在歌剧院吃饭。排队吃饭的时候,江河告诉我,顾城因为被分配的导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心情很低落。我们去求邵彦祥老师把顾城调到邵彦祥老师麾下,顾城就被解聘了。我们几个女诗人被分配到了颜晨老师手下,颜晨老师慈祥得像菩萨,对我们照顾有加。
诗歌朗诵会在北戴河结束,但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最经济、最实惠、最有效的一次大众旅游。
那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呆在海边,彻夜未眠。磷光溅在岩石上,飞鱼溅起的水花掠过海面,月亮挂在深蓝色的天空,清凉又干净。我抱着膝盖坐在大浴巾上,江河和顾城半躺半坐。我拂去灌木丛上的星光,哦,身后有梁小斌。
顾城约我去冲浪,江河会心一笑,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顾城挽着裤腿在浅滩上走着,拿出一本红色的小本子,翻开内页,里面嵌着一张女孩的照片,长长的辫子,明亮的大眼睛,正是谢烨。
他们的相识是浪漫的。在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地假装看报纸,在报纸上挖个洞偷看。被发现后,他什么也没说,女孩只是脸红了,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急忙把写着地址的纸条塞到女孩手里。于是《两地书信》热情地开始了。唉,没有手机的岁月,顾城的诗人气质想必更上一层楼。经受住距离的考验,经受住谢家人的关心和悲观,爱情终于开花结果。
1983年,顾城和谢晔来到鼓浪屿,说是度蜜月。我儿子当时不满一岁,体质虚弱,住院打吊针,我每天都赶去医院。于是就让他们住在百米开外我爸家。朋友来鼓浪屿,从最开始的艾未未,到后来的芒克、江河,基本都是我爸接待的。北岛曾多次说要来鼓浪屿看我,后来听邵飞说鼓浪屿就是个大花园,就没来了。哼,我记仇啊!
顾城夫妇住在我父亲的卧室里,我父亲则搬到了鸟舍里,我父亲爱鸟,鸟舍只有六平方米。
热爱烹饪的父亲不辞辛劳地将手中的肉票、鱼票、糖票、豆腐干票摆放整齐,用各种方式为他们做成美味佳肴。哥哥和嫂子下班过海回家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父亲不想让客人挨饿,就让他们先吃。等哥哥和嫂子回家,掀开盖头一看,发现四菜一汤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菜汁都没剩下。
听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后,顾城夫妇去了英国,邀请结束之后,他们住在朋友家。朋友一家出去旅游,回家后发现,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毁得一干二净。朋友开玩笑说:就像被老鼠抢了一样。
大概是1985年吧?福建东山办了“蝴蝶岛诗歌节”,我请了江河、顾城、杨牧、傅天林、陈所居等老友,顾城在信中问:能不能把谢野也带上?主办方没多少经费,东山诗人刘小龙又很为难,我就硬着心回答:不行!
于是顾城、江河等朋友来了,玩得不亦乐乎。东山的鱼虾蛤蚌鲜美肥美,大家每天都举杯畅饮,但唯独顾城不开心。那天晚上我看见他站在窗前,心情不爽,便问他。他回答说:这里每一顿饭都好吃,但平日里在北京,谢爷想吃个炒蛋都不容易。
我感到非常内疚,至今仍无法释怀。
80年代,只要在北京有会议,我的朋友都会到饭店来看我,虽然他们相处得并不那么融洽,但我经常和他们开玩笑:两个英雄不能共存。他们带着备用的衣服,轮流去卫生间洗澡。门开了又关,屋里热气腾腾,每个人的脸都红得像桃花。这时,顾城常常会起身,把头探出窗外,看看他们那辆破自行车还在不在。奇怪,公交车票才一毛钱,何必顶着寒风蹬车前行?顾城解释道:两分钱两个人,两分钱够买几斤白菜。那年头,一斤白菜才几毛钱。夫妻俩的饭菜就是一大锅白菜粉丝,天天如此。
那时开会是不能免费吃饭的,我把大家带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点了塑料杯装啤酒、炸酱面、拌菜、北京随处可见的家常菜。其他人都在座位上等着,只有我和手头最拮据的顾城赶紧去付钱。他事先准备好的十元纸币,叠得整整齐齐,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顾城和谢野在争着给我讲一个小故事——他们总是争着讲同一个故事,互相打断,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故事的结局是悲伤的,但他们讲的时候却很激动,很动情。
80年代,顾城到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级文化馆都能收到一堆他的稿件:随便挑一个寄过去就行了。于是稿费就零零星星地来了,三五块钱,白菜粉丝里还能加土豆。有一次来了一笔50元的巨款。夫妻俩商量好后,手牵手走过八一湖公园,把钱存进一家小储蓄所。第二天,不幸车胎爆了,需要换。两人一起去取十元;第三天,恰巧白菜打折,又取了十元;第二天,他们刚进储蓄所,还没开口,柜员就先说:“明天的十元可以一起取吗?”果然,因为他们每天都这样来回走,鞋子又坏了。
这时,马悦然夫妇到我鼓浪屿家来,我匆匆吃了顿饭,就送他们去轮渡,他对我说:“舒婷,你好好照顾顾城,你过得这么好,顾城什么都没有。”
是的,我选择了平凡的生活,工作,丈夫,孩子。顾城比我更像一个诗人,他不甘受委屈,忍饥挨饿,忍受不了世事。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选择,“用纯净的声音与你的梦想对话”。

左:顾城、谢晔。右:颖儿
2. 流放到岛上
以童年的姿态
再次靠近温暖的土地
你拾柴火,割草
种下两棵细老玉米
偶尔抬头看看
送候鸟回家
目前新西兰海域无风
你的眼睛雾蒙蒙的。
当他们在外面时
你在里面
鲜红的喙无助地撞击着高墙
祖国的天空
沾满你的鲜血
现在你在外面
他们在里面
所有秘密门都锁着
现在你已经到达了另一边,你再也不能
返回出生地
视线方向不变
你的脚已经在另一个磁场上
黑眼睛的妻子
坐在门口哺乳
将头发紧紧地编在头顶
就像坚强的向日葵
微笑转身
寻找你的光芒和光芒
你用中山装的袖子擦汗
站稳
逐渐填满命运的轨迹
渐渐金黄
1990.5.16
1986年5月,我应邀去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到纽约,再到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斯坦福、伯克利等几所大学讲学、演讲,省政府批准的出国时间是三个月。
我在纽约的时候,曾多次见到美国诗人金斯伯格,他主持我的诗歌朗诵会,还邀请我到他家喝下午茶,他是艾未未的好友。我们三人商量后,决定举办一次“北京—纽约”诗歌活动,中国诗人的名单是我提供的。
1987年,邀请函来了,但我的护照申请却被直接拒绝。原因是我1986年访问时没有准确计算时差,还是晚了一天,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我当时没有责怪处理此事的官员,因为这是铁律。
他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向王蒙求助,让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建帆打电话到省政府解释担保事宜,但都无济于事。金斯伯格心急如焚,甚至说服美国国务院下属机构给省外事办发了一封信,这或许更激怒了他,他最终没能成行。
我不记得有哪些诗人被允许参加这次活动。我只听说江河空手而下,宣称“英雄不再回来”。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呆在纽约。顾城夫妇没能回家。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北京没地方住。
幸好,中国诗歌刚刚走出国门,朦胧诗风正在蓬勃兴起。诗歌节、国际笔会、大学讲座、驻留作家的邀请接踵而至。他们游走世界各地,在活动间隙在熟人、朋友家中等候,甚至被安排或介绍住进从未见过的房子。
谢烨怀孕了,即使邀请条件好,那些国家的签证也很难拿到,她们在香港拿到新西兰签证已经是万幸了。顾城说,面试的时候,谢烨已经怀孕快八个月了,穿着宽松的衣服,不敢起身走动,生怕被人发现。签证官应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顾城出国后很少给我写信。是不是因为邮费太贵?他很少写满好几页,经常只写半页。有时他叫我妹妹,有时封我为“鼓浪屿大公”,自称“可汗”。他的字迹又大又稚嫩,总是在说这说那,读着让人忍俊不禁。我多是从朋友那里听说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定居新西兰,生了个儿子,种起了庄稼。我真的以为顾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以孩子的姿态/重新靠近温暖的土地……在命运的轨迹上渐渐充实。”
1992年5月,《今日》大部分同事被邀请到美国巡回读书演讲,老朋友之间的距离更加明显。当然,这跟我没关系,我根本没参与到那场闹剧中。一行人从旧金山到纽约,十多天,顾城和谢晔还跟我关系密切。他们描述在新西兰的日子时,语气幽默开朗,但现实依然艰难坎坷。
顾城在报纸上看到,吉流岛(当时不应该叫吉流岛吧?)上拍卖了一套小房子,房子不大,但很便宜。他有大学教书的职位,可以贷款。顾城从小就梦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风摇叶落,草结籽”。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座岛,贷款两万元。夫妻俩很快就搬到岛上居住。
顾城说: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走出那个不幸的世界,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顾城与奥克兰大学的合同即将到期,起初他并没有太在意,但偿还贷款的沉重负担很快就压垮了他。
退潮时,这座岛上露出沙子,你可以步行或开车穿过,到达民风淳朴、集市繁华的毛利部落。涨潮时,这里就是一片汪洋,这里成了真正的孤岛。不料,这座岛向阳的一面全是岩石,背阴的一面又不能种植庄稼,顾城的农场计划就这样泡汤了。立在山坡上的茅屋早已破败不堪,两人没力气,只好合力把大石头从山上推下去,先铺一条滚石路。后来顾城怎么学会凿凿修缮的,操作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我想那一定很辛苦,比堆字难一百倍。岛上没有水源,他们就在屋顶上建了一个蓄水池,供饮用、洗澡、洗漱。谢天谢地,新西兰总是天气好,要是不行呢? 顾城笑着说:“那你几天就别洗澡了,岛上的空气一尘不染。”
“种二十次萝卜,然后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顾城和妻子想到了养鸡。他们去市场买了200多只小鸡,建起石栏圈养。小鸡由机器孵化,几代之后,以农场式的流水线方式饲养。没有母鸡的指导,遗传密码里的自助觅食功能早已丧失。小鸡们集体发呆,绝食。他们俩只好一人抓着食槽的一端,模仿机器左右摇晃,这才教会小鸡最基本的课程。随着小鸡们长大,它们纷纷逃出鸡栏,诗意地生活在石缝里的草窝、灌木丛中,成为城市人梦寐以求的散养鸡。
现在该准备采收鸡蛋了。
不料执法人员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又出现了,原来按照当地法律,每户只能养12只鸡,他们被勒令在三天之内处理掉这些新来的翼岛民,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色彩斑斓、多么纯真、多么平和。
现在聚鸡没那么容易了,晚上得打着电筒走遍山野,才能抓到那些被强光刺瞎了眼睛的昏昏欲睡的鸡。顾城只敢抓着鸡的脚,让黑眼圈的老婆连夜割断鸡脖子、拔掉鸡毛、剖开鸡肚子。顾城说:舒婷,血流成河了!
当德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放鸡时,顾城诚实地回答:“都是钱啊,我们还要生活。”甚至有人评论说,顾城的血性是与生俱来的,三天之内,他宰杀了自己养的二百多只鸡。
这么多鸡怎么办?我替它们担心。顾城说,鸡都储藏在毛利人的大冰柜里,和猎物一起冻起来。谢晔用鸡肉做了春卷,拿到集市上摆摊。顾城无聊,想帮忙,就在附近画肖像,每幅定价八元。但谢晔说:岛民都互相认识,画完之后基本都是免费赠送,不能收费太高。但顾城喜欢,画画的同时,他认识了两千多岛民中的很多人。顾城不懂英文,孤独了很久,因为画肖像,他交了一些朋友。
顾城和谢烨讲起这些还是和以前一样,争相幽默有趣,哈哈大笑,让我也跟着笑了起来,鼻子酸酸的。

顾城的画
3. 破碎的万花筒
太阳黑子的运动,
中午发生爆炸
鸟儿们已安全穿越雷区
虽然日食只持续几秒钟
一步之遥,你将永远在百慕大
最后一棵树
伸出你的双臂
耳语
来吧
美丽人生只是一朵脆弱的冰花
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是黑暗的地狱
对自己
这是一个持久的
左手与右手的斗争
黄昏时分,他到水边洗手。
拒绝洗去他的影子
只有言辞的罂粟花
疏散
在他的挥杆之下
一
直的
布帽
静静地坐在舞台中央
灯光变暗
他
不
后退
家
1993.10.13 凌晨
回想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遇见顾城时,指着那顶布帽子笑道:“顾城,那是什么?”谢晔说:一位老外国太太送给顾城一顶直筒毛线编织的帽子,顾城很喜欢,一直戴着。帽子破了,他灵机一动,把旧牛仔裤的裤腿剪下一段,试着当做帽子。他太喜欢了,从此,这顶帽子仿佛长在他头上,成为一种象征。
关于帽子,有多种说法。顾城高兴时,会说:“像北京一样四四方方的,是他的故乡。”不耐烦时,会说:“我怕冷。”有时,他会再三强调:“安全感、避雷针、保护伞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高高的帽子其实很适合他。
虽然他们已经在国外多年,买了地房子,安顿下来生儿育女,但还是觉得吃不饱。顾城鄙视那些“吃遍天下的嘴”,但他更明白“做人就是要吃饭”。
主办方给我们的餐费补贴很丰厚,酒店供应早餐,晚餐总有活动和宴会,所以我们基本只付了午餐的钱。时差没适应好,早上起晚了也没胃口,就随便挑了一小块蛋糕,掰成两半慢慢吃。顾城问:另一半你不要了?我点头,他伸手从我盘子里拿过来立刻塞进嘴里。我急了:顾城,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谢晔笑着解释:我知道,他已经吃了六个了,我就知道。顾城每天肯定会熬到早餐时间结束,像牲畜吃了两茬庄稼一样拼命地填饱肚子。
中午?中午就睡,一直睡到晚饭时间,晚上开会之前。作为一个失眠严重者,我立刻想到:晚上呢?晚上继续睡。谢晔说,顾城从小就很能睡,最高纪录是连续两天睡了50多个小时。
艾未未在纽约,他请我到唐人街吃饭,点了好多菜,清蒸鱼、烤虾,甚至还有拳头大小的蜗牛。老板是朋友,过来提醒我:菜太多了!艾未未说:上次我朋友从大陆来,我没多少钱请她吃饭,这次要好好请她吃一顿。艾未未打开钱包给我看,哇,除了各种银行卡,还有厚厚一沓百元大钞。
我立即提议,既然我们住的酒店就在附近,能不能请顾城夫妇一起吃午饭?薇薇很了解他们夫妻俩,当然没反对。就算只有他们两个,菜还是太丰盛了。因为薇薇不停地夹菜,我的碗里还剩了不少。谢晔不仅把桌上的菜,包括汤,都倒进了顾城的碗里,还拿了我的碗给顾城倒。我疑惑地看着她。谢晔说没关系!在新西兰,谢晔一个人做饭,吃不完就往顾城的大锅里倒,顾城就直接“炖”着吃。
可以说顾城不在乎做饭,并不只是因为他重视食物。他能饿,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就尽量吃。就好像他永远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一样。回想起来,让人更心酸。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顾城多年的节俭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因为顾城在柏林DAAD的一年项目在1992年3月就结束了,DAAD支付的生活费很高,他们应该攒了不少钱。
那天吃过晚饭,我们出去逛街,走进一家小店。谢晔在货架上挑了好一会儿,挑出一个小玩具,笑眯眯地给我看。是一只小青蛙,捏一捏就嘎嘎叫,底部印着Made in China,价格是1.99美元。谢晔说:给你儿子买个中国的东西吧。我正要付钱的时候,发现顾城一直板着脸站在门口不进来。等谢晔把钱拿出来的时候,顾城竟然滑了下来,坐在了地上。我吓了一跳,以为他生病了,赶紧把他拉出来。谢晔大叫:别理他,让他去死吧。我更害怕了,回头看了看谢晔,她眼里含着泪水:我花钱的时候,他都这样了!
原来如此,那我就买吧,我还在烦恼给小牧儿买什么礼物呢。
顾城并不吝啬,朋友吃饭他都会争着付钱;他来我家度蜜月时,送了我两尺卡通印花棉布,我拿来给儿子做了个小被套;多年后我们在美国相见,他还送了我一把立陶宛漆器小勺子……这些东西虽然很小,却让人感觉到顾城重情重义,彬彬有礼。
从店里出来,谢晔抱着包装好的玩具扬长而去,恨恨的说道:“顾城,你去死吧。顾城,你死了还不如死了好!”
我跟着顾城落在了后面,作为干妹妹,自然是先骂顾城。顾城解释道:舒婷,如果我不能按时还贷,我的岛就会被拍卖,我们就会无家可归。所以每一块钱都要省着点。小穆儿一直寄养在毛利部落,虽然酋长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但是按照西方的伦理道德,酋长还是起诉顾城遗弃。说起穆儿,顾城渐渐笑了起来。因为顾城拿不出钱,毛利人居然还替他请了律师,这听起来就像是毛利人在起诉自己。在他们的观念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父母只要承担一点责任就行了。法院仲裁的结果是顾城每年必须给毛利人一点抚养费。顾城说: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如果他们不付这点抚养费,就会失去穆儿的抚养权。
“唉,花钱的地方可真多啊!”顾城感叹。
我曾问过:孩子叫什么名字?木儿。哪个木儿?银耳木儿。哦,古木儿?不,没有姓,就是木儿。
后来看到一些资料写成Sangmür。穆尔是昵称吗?也许Sangmür是毛利人的习惯称谓?
我从未见过他们的孩子,甚至没有见过他们的照片。
在旧金山,我们被邀请到美国诗人卡罗琳·凯瑟(Caroline Cather)赢得了普利策奖。 Gu Cheng没有进入水,而是坐在阴影中,我走过去,大声地说这句话,然后以低调的声音责骂他,直到他变得开朗。
因为楚想到她第一次坠入爱河时,她能保留两个长长的辫子,她的头发最多可以割伤她的辫子。买衣服。
1996年,DAAD邀请我在柏林(Berlin)居住在柏林(Berlin),在市中心(Bei Dao)居住在50号。英格和他的妻子从DAAD计划结束后返回柏林,他们在这对年轻的夫妇的家中教了Xie Ye如何开车,带着她的观光,并陪伴她在近距离购物。
作为一个来自上海的美丽而聪明的女孩,在徘徊和限制她的天性这么多年之后,Xie ye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必须疲倦。
今年,在他的诗人宣称自己的母亲拒绝他的所有沟通中,他拒绝了他的母亲,因此,在国外朗诵他的作品时,他只用各种奇怪的声音来表达。
巨大的经济负担,失语症的困境以及他的生活和精神伴侣的即将出发,例如古代,他再也无法坚持了。
“黑子的运动在中午的四分之一爆炸。”
即使我们可以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以及警察局的结论来理性地分析悲剧,后者可以真正恢复黑点运动的轨迹,深渊的无限黑暗及其绝望的轨迹?
结局永远不会被扭转或忘记。
诗人的论文

舒婷
Shu Ting(以前称为Gong Peiyu)于1952年出生于福建省Quanzhou,她是一位当代的女性诗人。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诗歌集“ Schnitt”,“ Singing Iris”,“ Archeopteryx”和散文收藏“ Heart Smoke”。



猜你喜欢

炫体时尚健身俱乐部-炫健健身俱乐部
 147
147 
香港亚洲时尚首饰及配饰展-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107
107 
时尚 英文单词-英语单词时尚
 133
133 
时尚消费观念-时尚观念怎么填
 86
86 
2024最时尚服装搭配男-服装搭配时尚男2024年新款
 205
205 
北京时尚服装厂-北京服装工厂店攻略
 73
73 
时尚女士单肩挎包-女士时尚肩单挎包图片大全
 173
173 
时尚短发女-短发时尚女大全集
 108
108 
时尚孕妇街拍-孕妇街拍时尚穿搭
 103
103 
新蒙迪欧20时尚版内饰-蒙迪欧新款内饰图片
 191
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