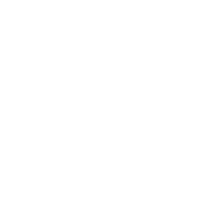北京京都时尚在哪-北京京都时尚医疗美容官网
2024-07-10 本站作者 【 字体:大 中 小 】
序言:现实生活应该有表达自己的力量。┄┄如果作者每天都把握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去处理眼前的事情,总能写出一些好作品。即使偶尔失败,也不是什么大损失。——艾克曼编《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1982
1823年,31岁的贫农艾克曼终于来到魏玛,拜访他的偶像歌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从此,艾克曼的名字就和一位伟人联系在一起了。尽管他备受争议,但没有人能阻止他名垂青史。正如美国比较文学教师戴维·达姆罗什所说,艾克曼通过编纂这份与歌德的对话记录,附身于歌德。那是无数人羡慕嫉妒恨的,令人厌恶的一句话:“我的歌德”。
196年后的今天,我也去了北京。我从祖国南方一个温暖的小城南宁来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了一年,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正因为如此,我才突然对艾克曼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和那些想把艾克曼从历史中抹去的评论家、学者不同。我并不否认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但当歌德和艾克曼同时作为文学人物出现时,艾克曼可能比歌德更能给读者或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艾克曼对文学的热爱和卑微的身份之间的差距,恰恰赋予了他文学形象的张力。歌德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更像是一座丰碑,如果不能和年轻的生命沟通,无论他有多么深刻的见解,恐怕也和路边的一块石头无异。有评论家认为,艾克曼受到了歌德的影响。 其实,歌德是否也应该感谢埃克曼使他的思想更加生动呢?
二
前不久,人大来了一位年轻的副教授,他是留学意大利的海归,在北大开系列讲座,我旁听了他的一节课,我唯一认同他的话就是北大的中文系是全国最好的,比京都大学还要好。别的不说,就比较文学而言,全国一共有五位长江学者,北大就有四位,这四个人我都见过。这就好比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五大高手,南皇北丐,中央魔神。除了周伯通没机会见面外,南皇北丐都出现了。当然,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比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热闹多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南皇北丐、无崖子、王重阳、张三丰等等,都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 就好比孙悟空要跟奥特曼打架,要怎么分出胜负?毕竟两人的格斗方式不同,体重也不在一个档次上。按照国际规定,这两个人是绝对不能放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法比较,只能说各有千秋,秋色各半。
一天,我和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乌兰在留学生食堂吃饭,一个头戴帽子、身穿黑色皮衣的瘦削男子看到我右手边的座位空着,示意我让他进去。我和乌兰正讨论着一个问题,突然那个戴帽子的男子说:“对。”我用余光瞟了他一眼,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专业,但因为他怒气冲冲地说:“长江学者也不能评二级教授?”,我猜到他的身份了。后来,经过仔细询问,我才知道,戴帽子的男子正是京师大学堂比较文学四位长江学者之一的张俊哲(化名)。我和乌兰顿时感到荣幸和幸运。我和乌兰互相客客气气的。乌兰说我很幸运,我的生活就像小说一样。 我说,要不是你刚才那句话,长江学者也不会出现,看来这个运气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创造的。
张教授吃完面,正要离开座位。我立即站起身,快速闪到一旁,深深鞠躬:“张老师,再见。”这绝对不是空洞的奉承。我从小就很尊敬老师。老师的话对我来说总有一种魔力,所以从小到大,我总是响应老师的呼唤。然而,当我成为一名教师后,我发现老师的呼唤并没有那么有效。在学生面前,我甚至会颤抖。吴兰也站起身来,行礼。
吴兰对张教授很感兴趣,马上上网一查,原来这位教授也是研究东方文学的,除了日语,还会韩语。“哇,原来是韩国人啊。”吴兰感觉自己发现了新世界。张教授曾坦言,自己和王教授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完全不同。
张教授提到的第三位长江学者是方卫国教授(化名)。我第一次见到方教授,是在季汉诺夫在伦敦大学做“世界文学与世界主义”讲座的时候。方教授是主持人,他围着围巾,衣着优雅,让我不自觉地把他和《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联系在一起。巧的是,方教授也是上海人。季汉诺夫做了四次讲座,我们见到方教授也就四次。方教授还邀请了京都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名教授,绰号“辛申”,长得颇像马景涛,来京都大学做讲座。那天,“辛申”所在的教室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走不出来。辛教授还真有明星风范,还把自己的亲笔签名照送给提问的学生。 虽然他很客气地说了一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但他的自信却丝毫未减,以至于当他转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我“吓得”差点闭上了眼睛。方教授“加油”地说:男同学不要提问。然而京师大学子却不把他的话当回事,站起来提问的同学大多是男生。
这样看来,方教授是我见过最多的长江学者了。算上我上过的那堂课,我一共见过他七次,比我的导师王教授还多。方教授德语流利,经常脸红,看上去很直率、很有激情。我猜是因为他学德语太深,有时候讲中文没那么流利。方教授曾自嘲:上我的课,就是看课件,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尽管如此,方教授的精神没有丧失,名声远播。
第四位长江学者是谁?我好奇地问了张教授,毕竟在京师大学的网站上我只看到三个名字。不过,当张教授提到第四个名字时,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位老师曾教过我等人两个学期,而且还是我在西都大学读博士的学院院长曹颂德教授。原来如此,曹教授身兼两职,与京师大学问渊源如此之深,这是我之前并不知道的。
三
到北师大不到一周,我就在王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王教授的办公室不大,但设施齐全,别的不说,在北师大能有一间自己安静的自修室,已经是我羡慕的事情了。
王教授的桌子上堆满了新鲜的水果,草莓、哈密瓜、香蕉等等,看得我垂涎欲滴。王教授教过的研究生、博士生、访问学者齐聚一堂,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时,每年大年初一拜年的场景。爷爷奶奶坐在桌边,其他的叔叔阿姨、堂兄堂妹,大家轮流给长辈们拜年。妈妈让我把大家叫过来,这几乎成了我们大年初一拜年的仪式。
爷爷奶奶去世后,老家的房子就没人住了,再也没见过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热闹拥挤的场景。但在王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竟然感觉像小时候过年时去拜访朋友一样。导师的感觉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就像父母、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一样。
大家轮流向王教授汇报学习或求职情况,或表达个人诉求。此时此刻,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想起晚上六点还有课,就率先和导师告别。临走时,我拿了一根香蕉。导师觉得一根香蕉太少了,就让我再拿一根。
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往楼下走,看了一眼电梯口挂着的海报。没想到刚一转身,就撞上了“虚无之阵”。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手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眼镜,眼镜还在,完好无损。借助眼镜的反光,我仔细一看,发现眼前是一堵玻璃墙,玻璃墙的右侧就是门,也是玻璃做的。我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额头流下来,伸手接住,再放回眼前,原来是一块鲜红色的血块。天啊,流血了。我的脑袋破了?
我突然很想念妈妈,也很感谢她。自从她生下我,我从来没有跌倒过。为什么会“走错”这堵墙?我一点也不难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上帝在提醒我、在帮助我。我刚到北京,还不到一周,上帝就让我用这种方式向北京致敬,仿佛在说:你好北京,请照顾我。
我精神上乐观,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校医院在哪?我刚到,还不知道。告诉门卫或者保安?他们根本没发现有人受伤,我怎么好意思蒙着脸去找他们?再说,我走到他们面前,又能说什么?说我撞到墙上流血了?像个无助的孩子?这不是我的风格。打电话给我的导师?我才刚来北京,就给别人带来麻烦,实在没脸做这样的事,一定要自救,毕竟以后的路还很长,还要自己走下去。于是,我想了想,决定还是拨打120急救电话,这应该是唯一最有效的办法。我很庆幸自己在北京,在大城市。电话接通后,对方要转去最近的医院,他们以为我给别人叫救护车,我强调是我自己受伤的; 我怕他们不重视,就说我伤势比较重,然后慢慢地走出主教府大门,向首都广场走去,面对着红旗飘扬的地方,那是我同意拨打120的地方。
晚上六点左右,北京广场,冷风吹来,刺骨的寒风钻进我的脖子。我一手捂住受伤的头,一手握着手机,环顾四周,有玩耍的孩子,有路过的家属和学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甚至没有一个人朝我这边看。天空中一群乌鸦低低飞过,我想起一位老教师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这里是很多年前刽子手处死人的地方,地下埋了很多尸体。她说,你没注意到吗?主教楼就像棺材,图书馆就像墓碑。北京人比较迷信,认为门不能正对棺材,所以这边的门就开在南边。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真的,那些鬼要报复的人肯定不是我。所以,我从来不怕。
我自拍了几张,看到自己半张脸都沾满了血,但我还是咧着嘴笑,像个调皮的孩子。想到需要包扎伤口,我想把衣服脱掉,但又怕脱了衣服会着凉,毕竟天气还是很冷,我又穿着羽绒服,如果脱掉衣服站在空旷的广场上,救护车还没到,我估计会冷得站不起来。而我又不能回教学楼,只能站在广场中间,这样我和救护车才能方便地找到对方。
救护车终于来了,我看了看时间,大概等了不到二十分钟,两个医生急匆匆的下来,我感觉像是看到了亲人,还没等到他们注意到我,我就走到他们面前,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上了救护车,我看到车上放着一个担架,旁边坐着一个医生。上车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愧疚,我受了点小伤,就来了三个医生和一个担架,这得有多严重啊,医生会不会觉得我“小题大做”?我有点紧张,医生让我躺在担架上,我感觉“受宠若惊”,又有点不好意思。医生坚持让我躺着,说躺了她就给我包扎。于是,我就乖乖听医生的话。医生们对我的伤很认真很认真的治疗,没有觉得我在“耍手段”,看到他们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心里也稍微放心了一点。 迷迷糊糊中,一个医生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签字。我签了一份,又签了一份。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再说,我受伤了,也不好意思要求时间长一点,或者看清楚一点。反正我隐约看到一个数字,2500元每小时。我刚放下的心,又开始悬起来。2500元每小时,我估计这一趟至少得花几万吧?一万可能不够,估计得几万吧?怎么办?我刚来北京,就得花几万,我这辈子难道就这么不懂得理财吗?我真的没有财运。几万,我都不知道卡里有没有那么多钱。如果凑不齐这么多钱,找谁借呢? 我爸妈借不出来,我老公也没钱借,别人借也没道理。但转念一想,管他呢,我先治病吧,既然他给我打电话了,不管多少钱我都收下,就算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也凑得齐。也就几万而已,我应该能负担得起。这样一想,心里就放心了。反正几万而已,有什么好怕的?
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我想多了。医生只收了我265元的救护费,我通过微信打到她个人账户,她再帮我付现金。给我治病的医院是北大三院,给我做皮肤检查的那个小伙子很温柔,给我缝针的年轻医生也是刚毕业不久,做事非常细致。半个月后,我的伤口愈合了,几乎看不出做过手术。我其实还是很怀念在医院的感觉,那是我感觉最温暖、最放心、最平静的时候。我不太会照顾别人,也不敢享受别人的照顾,但如果非要二选一,我宁愿选择晒太阳,或者照顾自己。照顾别人还是被照顾,我都有心理负担。去美容院享受自己花钱买的护理,总觉得很浮华、很肤浅。 那些做美容的女人技术虽然不怎么样,但她们嬉皮的笑容和矫情的功力却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也许只有医护人员才是最用心照顾病人的。
四
春天的京都天气时热时冷,但总体来说气温逐渐回升,各种花儿也开得正艳。首先是樱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开得太早,在暖春到来之前就凋零了。其次是木兰,大片大片地开着红、白、紫,放眼望去,都是姐妹,却依然淡定。再有就是郁金香,个别花朵叶片大,花心空洞,但红黄混在一起,却形成不可小觑的鳞片。最惊艳的还是海棠花,花中仙子,在公交车上无意间看到,便下车痴迷地跟着看了起来,近距离看确实让人失望很多。
应朋友之邀,我也去了京都大学的静园。我觉得最好的春景,是在热闹与没有热闹之间,稍加点缀,却不争美。有杨柳摇曳,柔情似水;还有未名湖的水,碾压着太阳的金光,如万千颗星辰,衬托着塔楼的梦幻。朋友是个超级贴心的人,不但履行了热情好客的义务,还主动帮我拍照。我拒绝不了他的好意,加上世事无常,便心不在焉地拍了几张。但总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美丽的春景,无论是与花草一起拍照,还是与水景一起拍照,要么是浪费自然资源,要么就是大破坏。来北京一个月了,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好不容易和朋友出去春游了一次,春光却刺瞎了我的双眼,刺痛了我的心。 如此美丽的花草树木、山川秀丽的风景,我该与之为伴的是多么美妙的人啊,怎么会是我呢?我浑身充满了衰老和“腐朽”的气息,只配在古墓里读《亡灵书》。直到走出书房,来到大自然中,我才感受到。我不禁感到惭愧。这种失落感似乎与我听课时的兴奋感是来自不同的身体。我想起张正文教授说过,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是民族的不稳定性。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青春期延长的民族,充满活力,但不稳定。我其实有点羡慕,好像他说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人。那么我到底是应该做一个结构稳定的人,还是一个活力十足、青春期延长的人呢?我既痛苦又快乐,既绝望又幻想着希望。

我在京都待了一个月,上过不少课,听过不少讲座,对形形色色的人也了解不少。不管这个官有多高,级别有多高,学问有多深,来听他讲课的人都不会太多,只有十几二十人,有的还是被学校逼着去听的。做学生也好,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地位而骄傲,引来无数读书人来征服你,但最后都失望而去。记得有一次,帝国大学的一位大佬很无奈地说:我为什么在学生中没有号召力呢?这位先生以前是位高官,即使他改行做了读书人,手里还有重要的资源,迎合他喜好、奉承他的人很多,但他还是不肯罢休,想要赢得学生的心。我觉得这就是贪欲。做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做人;做读书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学问。 你不用在意别人喜不喜欢你。科研人员的任务是发现真理,而不是想方设法讨好人,因为一旦有了讨好人的心态,就必然会庸俗,庸俗是科研的大敌。不管是否流行,科研人员的初衷和基本任务都不应该变。
北京很大,但有些人你永远也见不到,也碰不到。你看到的是满大街都是和你一样的人,个个都是风尘仆仆。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最不时尚的。北京人穿得没有四川人好,北京物价也没有南宁高。就算你读博士、读博士后,你的根还是在底层。前几天看了王小帅的电影《地久天长》,那是过去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奇迹,没有浪漫,只有忍耐和煎熬;不管风雨有多大,能活下来就是胜利。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要用掉好几包纸巾,但我没有流一滴泪。因为那不是我喜欢的生活。不管什么原因,我都无法认可、无法认同那种生活方式。生活需要一些改变。我和艾克曼真的没法比。 他寻找的是歌德,而我要寻找和建立的,恰恰是我自己。我是我的英雄。但某种程度上,我有点像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抛开他夸张的野心,我更合适的身份是京都的一个旁观者。